問學山水田野間
宋兆麟,1936年生,遼寧遼陽人。考古學家、民俗學家,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196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留校,1961年調入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著有《中國風俗通史》《中國生育信仰》《耳蘇人沙巴象形文和圖經調查》《伙婚與走婚:金沙江奇俗》《尋根之路》等。
從20世紀50年代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算起,宋兆麟從事民族田野調查和民族考古比較研究工作已近70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為他所供職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征集了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積累了大量一手民族考察資料。
回顧數十年的民族田野調查,宋兆麟說,這項工作既是科學研究,又是探險之旅。
求學之路
1936年,宋兆麟出生于遼寧遼陽北郊的一個小村莊。戰亂年代,他只念了兩年小學就輟學在家。父親和兄姐參加革命上了前線,作為家里唯一的小男子漢,宋兆麟每天放牛、砍柴、種地,風雨無阻,承擔起生活的重擔。
新中國成立后,宋兆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被家里送到遼陽市讀書。學校按照年齡直接安排他讀小學六年級,一年后就上初中了。他憋著一股勁兒,努力學習,讀初三時,成績慢慢趕上了同齡人,到了高三,一舉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在學術氛圍濃厚的北京大學,宋兆麟絲毫不敢懈怠,更加勤奮地學習。翦伯贊先生講的漢代史、鄧廣銘先生講的宋史、夏鼐先生講的考古學通論、蘇秉琦先生講的中國文明起源、宿白先生講的佛教藝術等課程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大二,該分專業了,他想學考古,又擔心自己色弱,不適合考古專業。他咨詢了尹達先生,尹達告訴他,只要不學藝術考古,問題就不大。尹達建議宋兆麟學習史前考古,并將其與民族志相結合。分到考古學專業后,宋兆麟就按照這個思路,主要選修與原始社會史、民族志相關的課程。著名社會學家、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林耀華在給他們講授原始社會史課程時,大量運用民族學資料,深深吸引了宋兆麟。從此,他愛上了民族學。
當時正在進行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北京大學歷史系近百名學生參與其中。宋兆麟被分到廣西,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民族調查,還參與了《壯族簡志》的編寫工作。這段經歷使他對壯族、侗族、瑤族的文化有所了解,初步掌握了民族調查方法。
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為學生安排了考古實習,包括參觀實習、試掘實習和生產實習,其中生產實習最為重要。宋兆麟的生產實習是在河南洛陽王灣遺址參加現場發掘。測量、發掘、記錄、攝影,這些在實習中掌握的技能在他以后的民族考古調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未名湖畔五年苦讀,宋兆麟這個農村孩子,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走進了學術的大門。
田野之樂
宋兆麟認為,做好學問需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勤奮,二是機遇。而1961年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就是他難得的機遇。
1961年夏天,翦伯贊赴內蒙古考察,寫就了名篇《內蒙訪古》。在翦伯贊等學者的呼吁下,民族文物的搜集、保護與研究受到有關部門重視。不久之后,中國歷史博物館承擔起搜集民族文物的任務。具體做這項工作的,就是年富力強又有民族調查經驗的宋兆麟。
如何搜集民族文物?前人并沒有留下多少可以借鑒的經驗。在民族學領域,鮮有學者把物質文化或者民族文物納入研究范圍。在文博領域,雖然有少數人關注民族文物,但是因其市場價值不高,也未引起足夠重視。宋兆麟堅持深入邊疆民族地區,觀察各民族的物質文化形態,參考各種民族調查報告及相關文獻,擬定了一個民族文物搜集提綱,內容涉及生產工具和設備、手工業工具、衣食住行、禮俗、科學文化、宗教信仰等。按照這個思路,他為中國歷史博物館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
1961年10月,宋兆麟告別即將臨盆的妻子,毅然奔赴內蒙古,調查阿里河的鄂倫春族。那里地處大興安嶺西麓,冬季氣溫常處于零下40多攝氏度。有一次暴雪封路,車輛停運,他在轉運站滯留了十天,與十幾個老鄉擠在一個大火炕上,糧食吃光了,只能吃豆餅充饑。為了了解鄂倫春人的生活,他與獵人一起去林場狩獵,一起在野外吃混著獸毛、帶著血絲的獸肉。夜晚露營,寒風刺骨,他睡在篝火旁邊,身下墊著馬鞍,上面蓋著皮衣,依然不時被凍醒。那段日子雖然辛苦,但他真正走進了鄂倫春人的生活,眼界大開,搜集到了近千件文物。待到第二年春天回家時,他的女兒已經出生了。
從大興安嶺返京幾個月后,宋兆麟又帶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文物征集組到云南西雙版納調研。當時,西雙版納醫療條件落后,惡性瘧疾和麻風病時有發生。他在當地做民族調查,與麻風病患者多有接觸,好在并沒有被傳染上。在西雙版納,宋兆麟與同事搜集到傣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基諾族等民族的文物10000多件。西雙版納天氣炎熱,幾乎天天下雨。工作之余,他常和同事們到瀾滄江邊,或休憩,或游泳。憑借考古專業的敏感,宋兆麟在江邊的斷崖上發現了陶器、石器等遠古人類居住的文化遺存。
1963年,宋兆麟到云南寧蒗彝族自治縣進行文物征集工作。地處小涼山腹地的沙力坪村,是一個彝族的聚居地。宋兆麟吃住在村莊,和當地人一樣,每天三頓飯都靠半生不熟的烤土豆充饑。完成工作任務后,他準備返回麗江,但沒有車可坐,就決定步行。第二天,天還沒亮,宋兆麟就帶著一盒米飯出發了,途中兩次走錯路,走了兩天才到麗江。回憶那次步行山路的經歷,宋兆麟說,返程不久就步入山林中,林中百鳥齊鳴,山風呼嘯,讓他恐懼得連頭發都豎起來了。現在已是著名旅游目的地的瀘沽湖,當時還是一片鮮為人知的神秘地域。瀘沽湖西岸就是今天的寧蒗縣永寧鎮,宋兆麟詳細調查了永寧納西族的母系社會家庭和走婚制度,搜集了3000多件文物,用了40匹騾子將其馱出山區,輾轉運回北京。
為了進一步了解瀘沽湖地區的走婚習俗和母系社會,1981年3月,宋兆麟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嚴汝嫻、劉堯漢夫婦在馬幫向導的帶領下,從麗江出發奔赴四川涼山州木里藏族自治縣的俄亞大村開展調查。俄亞大村位于瀘沽湖東南的大藥山西邊,那時有100多戶人家、1000多人,在人煙稀少的當地被稱為“大村”。群山懷抱中的俄亞大村,交通閉塞,歷史上依賴馬幫運輸。宋兆麟此行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藥山,途中不時穿過云杉、冷杉組成的林海,常常在懸崖邊狹窄的小路上艱難行走。大多數路山勢陡峭不說,還不時有落石滾下,各種野生動物時隱時現。在一處山路上,突然出現一只豹子,走在前面的頭馬受到驚嚇,失蹄摔下了山崖。宋兆麟就走在旁邊,所幸沒事。2003年,宋兆麟第七次奔赴瀘沽湖進行民族調查,又一次踏上了艱難的旅途。七次調查,他走遍了瀘沽湖周圍36個村落,對走婚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海南黎族被認為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保留了不少原始文化。從1992年開始,宋兆麟連續五年到海南開展黎族調查,每年去兩個月,走訪了25個黎族村寨,調查了五個黎族支系。2001年3月,宋兆麟第六次去海南調查黎族。在通什市(今五指山市)毛道鄉的毛道河邊考察黎族葫蘆舟渡河,此時已年過花甲的他,在河邊奔跑著追蹤拍照,不慎滑倒,導致右腿股骨頭損傷,在醫院治療近一個月才回到北京。
乘舟渡河、騎馬趕路、徒步跋涉、野外露營……數十年來,對于宋兆麟來說,這些都是家常便飯。談起野外生存經驗,他頭頭是道:夏季在野外露營,蚊蟲肆虐,一旦防范不當,人和牲畜都會有性命之憂,需要不斷地燃起篝火熏蚊子,還要佩戴防蚊面具;冬季露營,必須保持篝火旺盛,既可以御寒,也可以防范野獸襲擊;在山區行走,既要提防蛇蟲出沒,也要小心泥石流……
路途雖然艱辛,但當時的民族文物留存相對較多,搜集起來也容易一些,可謂苦中有樂。時過境遷,如今,民族文物越來越稀少,宋兆麟早年工作的價值日益凸顯。1962年,他在西雙版納進行傣族民族調查時,請當地傣族知識分子抄錄了當地文物室的基本文獻,后來當地文物室的文獻盡毀,這些手抄本成了文物。有一年,西雙版納籌辦傣族文物展,苦于文物不足,宋兆麟又押運當年搜集到的傣族文物重返西雙版納。
宋兆麟的民族調查,既有重點調查,也有專題調查。在大興安嶺、西雙版納、瀘沽湖等地,他一扎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有的地區反復去過多次,并有專著問世,這屬于重點調查。他對于廣西左江崖畫、嶺東南三族風俗、水族石墓等的調查,駐扎時間相對較短,只寫調查報告或學術論文,屬于專題調查。除此之外,為了擴大視野、增加感性認識,他還到黑龍江、新疆、西藏、江蘇、浙江等地調查,這些調查成為他做比較研究的重要積累。
在民族調查中,宋兆麟堅持每天拍攝照片,寫調查筆記。幾十年后,他重訪當年調查過的村落,往往會發現當地的風俗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少文化現象甚至已經湮滅。依據自己當年的這些調查筆記和老照片,他寫出了《邊疆民族考察記》,保留了珍貴的歷史記憶。根據自己的調查記錄,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宋兆麟還撰寫了一系列專著,如寫鄂倫春族的《最后的捕獵者》,寫納西族摩梭人的《走婚:女兒國親歷記》《伙婚與走婚:金沙江奇俗》《永寧納西族母系制》《瀘沽湖的訴說——男子走婚和母系家庭》,寫普米族的《瀘沽湖畔的普米人》以及寫川西南藏族納木依人的《尋根之路:一種神秘巫圖的發現》等。
治學之道
民族考古既包括對我國古代邊疆地區的民族進行考古研究,如吳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詔考古、遼金考古等,也包括不同民族間的考古比較研究。前者是我國傳統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隊伍大、人員多,成就卓著。后者雖經王國維、蔡元培、郭沫若、李濟、林惠祥等前輩學者提倡,但從事該項工作的人并不多。宋兆麟既做過古代邊疆地區的民族考古研究,如景洪新石器時代考古、瀘沽湖新石器時代考古、博什瓦黑南詔石刻考古,也做考古比較研究,而且將比較研究作為重點。
宋兆麟的比較研究是從器物學開始的,他善于利用民族地區保留的漁獵工具、農具、紡織工具去闡釋、復原考古發現的各種器物。例如,山西許家窯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許多石球,這些石球是干什么用的?宋兆麟認為,這些考古發現的石球與繩索、皮兜共同組成了當時的一種狩獵工具——流星索,其與西南民族地區現在保留的飛石索類似。他先發表了《投石器和流星索——遠古狩獵技術的重要革命》一文,后又將其寫入《中國原始社會史》一書。他指出,無論在河姆渡文化遺址還是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不少石球,說明流星索仍然為人們所應用,只是石球小型化了,這從側面反映出其他狩獵方法的增加和大型獵物的減少。對于史前遺址出土的大量彈丸,他提出,這意味著彈弓十分流行。這種彈弓與一般弓相似,但以竹、藤為弦,中央有一個兜,可置一至三枚彈丸,供射鳥使用。云南傣、佤、布朗、拉祜等民族都有這種彈弓。輔以為證的,正是他從云南搜集到的彈弓。
史前社會,距今久遠,研究難度很大。宋兆麟將考古資料與自己調查來的民族學資料相結合,為史前史研究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說:“考古學資料是史前研究的基本資料,它能展示史前社會的骨骼系統,能提供一個確實可靠的歷史坐標,但是歷史是具體的,是有血有肉的,這樣僅僅依靠考古學的‘死化石’就不適應了,必須求助于‘活化石’——民間文化資料,也就是搜集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資料。”比如,洪水神話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宋兆麟發現,在中國的洪水神話中,葫蘆占有極特殊的地位。在水族傳說中,遠古時代洪水滔天,很多人都被淹死了,唯有拾雷公斧的兄妹坐在葫蘆內活了下來,白胡子老人勸兄妹結婚,才有了水族。布依族古歌謠唱道:“洪水滔天心不驚,園里摘下大葫蘆,挖個洞洞掏心心。賽胡細妹手牽手,葫蘆里面來藏身。”此外,黎族、侗族、傣族等也有類似的傳說。這說明在洪水中利用葫蘆求生是一種普遍現象,葫蘆是遠古時代重要的救生工具。他運用考古資料與民族學資料相結合的方法,撰寫了《原始社會》《中國原始社會史》《原始社會風俗》等著作,受到學界的好評。
原始宗教和民間信仰也是宋兆麟重要的研究領域。通過對巫覡、薩滿、苯教及彝族原始信仰的比較研究,他寫成了《巫覡》《巫與祭司》《民間神像》《會說話的巫圖》《巫與巫術》《巫與民間信仰》《中國生育信仰》等專著,深入探究原始宗教和民間信仰。其中,《中國生育信仰》獲得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一等獎。
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寫道:“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匯才具有永久的價值。因此在我的種種理論由于喪失了用處,而和那些習俗及信仰一樣承受廢止的命運的時候,我的書作為一部古代習俗和信仰的集錄,會依然保留其效益。”宋兆麟關于民族考古研究的著作,正是具有這樣的價值。
老驥伏櫪
在民族考古學研究中,宋兆麟深知,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漢族歷史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少數民族的昨天,就是漢族的前天或大前天,兩者之間有不少共性,可以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漢族的歷史與民俗文化。在退休后,他把研究領域拓展至民俗學。
節日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內容,宋兆麟撰寫了《中國傳統節日》《中國二十四節氣》兩本著作。他的民俗研究,并不局限于民俗學本身,而是將自己畢生鉆研的考古學、民族學融入其中,別具一格。進入21世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越來越受到各界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等工作隨之展開,宋兆麟受邀擔任文化部(今文旅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參與編寫《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普查工作手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手冊》),參加評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等工作。
宋兆麟一生從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在博物館從事文物鑒定、陳列、研究工作,深知文物的價值所在。退休后,他自己也搞起了文物收藏,并形成了一系列專題收藏。他針對藏品開展研究,出版了《古代唐卡遺珍》《遼代插圖本楷書〈金剛經〉》《遼代繡畫》《古樂擷英——我所收藏的樂器》等專著。與文物打了一輩子交道,他把自己的經驗、體會和方法以及各種有趣的故事匯集起來,出版了《民族文物通論》《中國民族民俗文物辭典》《古代器物溯源》等著作。
宋兆麟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收藏文物,并非以占有為目的。每當做完研究,寫出了著作,他就把藏品捐獻出去,多年來已給各地博物館捐獻了不少文物。
一生踏遍了祖國的天涯海角,宋兆麟見證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寫下了洋洋灑灑千萬余言。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筆耕不輟,帶領學生開展文物研究,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作者:馬海軍,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文娛新聞精選:
- 2025年12月04日 16:36:10
- 2025年12月04日 15:48:05
- 2025年12月04日 11:44:12
- 2025年12月04日 11:34:29
- 2025年12月04日 11:29:29
- 2025年12月03日 17:04:53
- 2025年12月03日 16:29:53
- 2025年12月03日 15:51:06
- 2025年12月03日 15:03:25
- 2025年12月03日 15:0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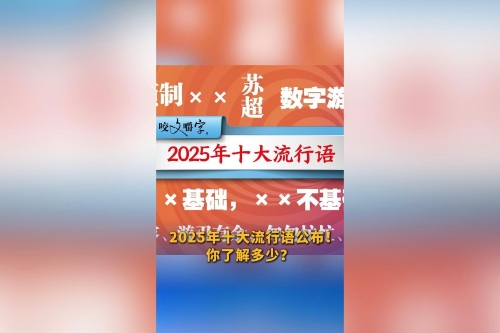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